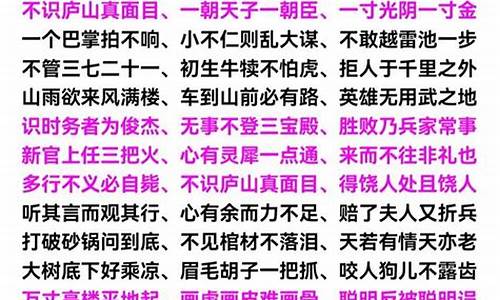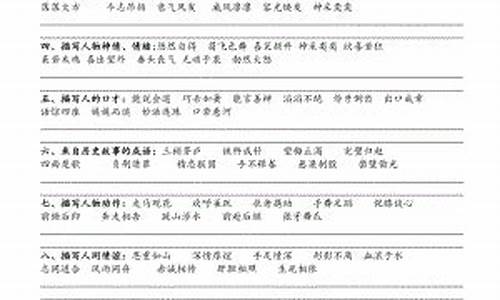您现在的位置是: 首页 > 成语典故 成语典故
血火明末全文免费阅读_血火明末
tamoadmin 2024-08-09 人已围观
简介乌衣巷在南京秦淮河南岸,三国时是吴国茂守石头城的部队营房所在地。当时军士都穿着黑色制服,故以“乌衣”为巷名。后为东晋时高门士族的聚居区,东晋开国元勋王导和指挥淝水之战的谢安都住在这里。19年,秦淮区人民恢复了乌衣巷并重建了具有民族风格的王谢古居。唐代诗人刘禹锡作《乌衣巷》,以有“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诗句,感叹王谢旧居早已荡然无存。这是诗人感慨藏而不露,寄物咏怀的名篇。是组诗《金陵五题

乌衣巷在南京秦淮河南岸,三国时是吴国茂守石头城的部队营房所在地。当时军士都穿着黑色制服,故以“乌衣”为巷名。后为东晋时高门士族的聚居区,东晋开国元勋王导和指挥淝水之战的谢安都住在这里。19年,秦淮区人民恢复了乌衣巷并重建了具有民族风格的王谢古居。唐代诗人刘禹锡作《乌衣巷》,以有“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诗句,感叹王谢旧居早已荡然无存。这是诗人感慨藏而不露,寄物咏怀的名篇。是组诗《金陵五题》中的一篇。
简介:
乌衣巷乌衣巷位于夫子庙南,三国时是吴国茂守石头城的部队营房所在地。当时军士都穿着黑色制服,故 乌衣巷以“乌衣”为巷名。东晋初,大臣王导住在这里,后来便成为王、谢等豪门大族的住宅区。到了中唐,诗人刘禹锡以有“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感叹,足见王谢旧居早已荡然无存。南宋时期,建康城曾一度得到恢复和发展,“商品繁盛,民殷物阜”。人们又在倾圮的王、谢故居上重建“来燕堂”。其址在乌衣巷东,建筑古朴典雅,堂内悬挂王导、谢安画像。士子游人不断,成为瞻仰东晋名相、抒发思古幽情的胜地。目前这里是一小狭窄的小街,住的依然是“寻常百姓家”,只是小街两侧的铺面房都开成了民间工艺品店,中外游人在此可以观赏和购买到各类工艺品。 19年,秦淮区人民恢复了乌衣巷并重建了具有民族风格的王谢古居。
历史:
乌衣巷历史悠久。据志书记载,其名源于三国时期。赤壁之战,孙权刘备结盟大破曹军,奠定了三分天下的局面。当时在公元220年,曹丕称帝,国号“魏”,公元221年,刘备称帝,国号“汉”,通称蜀或蜀汉,公元229年,孙权称帝,国号“吴”,史称东吴,当年秋七月,孙权将都城由武昌迁南京,取“建功立业”之意,将秣陵改为建业。孙权是史上第一个建军都南京的皇帝。当时,孙权的兵士们都是穿黑衣,驻军之地就称为乌衣营。 乌衣巷
公元280年,晋军攻占建业,孙皓投降,吴亡,改建业为建邺(南京城内有一个区就叫建邺区)。 乌衣巷风光(2)(13张) 公元290年,晋武帝死,皇宫和诸王争夺权力,互相残杀,酿成八王之乱。公元307年,晋怀帝司马炽任命琅邪王“司马睿”为安东将军,管理扬州、江南等地,公元317年,当时的皇帝司马邺被俘,西晋灭亡。次年,司马睿被推戴为皇帝,定都建康,即现在的南京。 司马睿之所以能立足于建业,顺立重组,使晋王朝得以再延,系得力于王导的谋划和周旋,以王导为代表的王氏家族和以谢安为代表的谢氏家庭都居住在孙吴乌衣营旧址,此时的乌衣营已改称为“乌衣巷”。 王导,辅佐创立了有百年历史的东晋王朝;谢安指挥淝水之战,以少胜多,打败符秦百万大军。作为一代名相,王、谢足以令后人追怀。而更令人惊奇的是,王、谢家族人才辈出。王羲之与另外两位大书法家王献之、王洵,书法成就登峰造极,谢灵运是中国山水诗派的鼻祖,他与谢氏后裔的大诗人谢惠连、谢眺,在文学史上并称“三谢”。 入唐后,乌衣巷沦为废墟。唐代大诗人刘禹锡的那首脍炙人口的诗:“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就是对此处的感叹。寥寥数笔,便描绘了乌衣巷自六朝到中唐的沧桑变化。从此乌衣巷便名播中外,游人不绝。现在巷口刻着的这首诗为同志手书。 南宋时期,建康城曾一度得到恢复和发展,“商品繁盛,民殷物阜”。人们又在倾圮的王、谢故居上重建“来燕堂”。建筑古朴典雅,堂内悬挂王导、谢安画像。士子游人不断,成为瞻仰东晋名相、抒发思古幽情的胜地。
文化:
乌衣巷》 作者:刘禹锡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朱雀桥在金陵城外,乌衣巷在桥边。 乌衣燕子,旧时王谢之家,庭多燕子。 王谢王导、谢安,晋相,世家大族,贤才众多,皆居巷中,冠盖簪缨,为六朝(吴、东晋、宋齐梁陈先后建都于建康即今之南京)巨室。至唐时,则皆衰落不知其处。
历程:
记南京乌衣巷 乌衣巷 刘禹锡的感慨源自这条古巷曾居住的王、谢两个显赫的宰相家族:一是王导,辅佐创立了有百年历史的东晋王朝;另一位是谢安,指挥淝水之战,以少胜多,打败符秦百万大军。作为一代名相,王、谢足以令后人追怀,更令人惊奇的是:王、谢家族人才辈出,他们居住的这条古巷,还有“王家书法谢家诗”的风。王羲之与另外两位大书法家王献之、王沟,书法成就登峰造极。 乌衣巷
衣巷名贯古今,不仅因为王导、谢安居住在这里,书圣“王羲之”、山水诗鼻祖“谢灵运,谢洮”也住在这里,还因为王谢两户大家族,在这里居住了三百年,出现了一批对晋朝的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人物,历朝历代都有两大家族的人物参与重要政治,对历史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从繁华热闹的夫子庙出发,步过秦淮河上的文德桥,撇下风韵诱人的媚香楼往西南行数十米,便可以看到乌衣巷的题字和树立的诗碑了。巷子是窄窄的,用青砖铺的路面,两边则是矮矮的仿古建筑风格的民房。一切似乎都很普通,普通得令许多不知情者都以为它只不过是一条典型的江南小巷而已。一条静静的,有点怀旧情绪的巷子。 然而它并不普通,因为它不是别的小巷,它是乌衣巷。 我们把历史回推一千七百年,回到三国东吴的时代。那时南京还叫做建业。如果说越王勾践筑越城是为南京建城之始的话,当时的建业只有八百年的历史。那时,建业远没有今日南京这样大的地域,整个东吴的都城只是在鸡笼山,覆舟山一带展开。那时孙氏王朝的统治者还在传说中的太初宫里居住,那时的秦淮河要比今天的宽很多,碧波荡漾,水光粼粼。那个时候,人们还不知道他们的都城今后在历史上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六朝的金粉,秦淮的艳色还要等上几百乃至上千年才会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那个时候,的夫子庙,明城墙还只是一片平地。然而,如果我们可以回到那个时候,我们会看见在秦淮河边的这条小巷里,已经有一队队的身穿黑衣的士兵在居住,操练,谈笑了。这里是东吴禁卫军中的乌衣营所在地,自然而然的,人们便把这条小巷称为乌衣巷。后来又有人说这乌衣二字其实是来自王谢子弟之爱穿黑衣,我便觉得虽然风流,总不如这东吴衣甲来得深沉和有意味了。 走在乌衣巷内,两旁的建筑一律漆成白色的墙壁。配以古色古香的黛瓦屋顶,门窗檐楣,颇有古巷的味道。这些都是不久前秦淮区根据古代建筑风格新建的房屋,同秦淮区明清建筑群相得益彰。进了巷口一转弯,就可以看见“王谢古居”四个金色大字在雪白的墙上很是显目,随之的一所朱门大府,又高挂“王谢古居”大匾的,则无疑是那传说中的王谢堂府了。于是不禁让人又想起“旧时王谢堂前燕”的句子来。 无疑,乌衣巷的一砖一石,都是同王导,谢安两大家族的历史紧紧相连的。而王导,谢安两大家族的历史,又无疑是同整个东晋王朝的历史,乃至中国的整个文化史紧紧相连的。 原来这条小巷,曾经住过几位叱吒风云的人物。 乌衣巷 首先是王导,东晋王朝建立过程中举足轻重的大臣。起初是晋室琅玡王司马睿的安东司马。西晋末年,爆发八王之乱,西晋王朝的统治一朝内土崩瓦解。王导审时度势,认为天下大乱,能振兴晋室的唯有司马睿。遂倾心推奉,为之谋划。是他劝司马睿把都城移到了建康(就是东吴的建业,今天的南京) ,为东晋打下了立国之本。是他依靠北方士族的力量,团结到江南士族,协助司马睿建立了偏安江左的东晋。他历任晋元、明、成三帝的宰辅,用“镇之以静,群情自安”的方针,保持东晋的安定局面。作为晋室中兴的元勋,王导功大无双,一时风光无限。据说司马睿登极那天居然要把王导拉到他身旁同受百官朝贺,民间更是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可见其权势薰天。 这位东晋的开国元勋,他的府第就在乌衣巷。 其次是谢安,一位在中国历史上具有色彩的人物。曾隐居东山,以诸葛自喻,直到四十多岁才赴任丞相,从而创造了我们词汇中“东山再起”这一成语。上任之初就成功阻止了桓温的篡位之举,太元八年更指挥了中国历史上奇迹般的一场战役:淝水之战。以8万精兵击败前秦苻坚100万大军,从而奠定南朝300年的安定局面。在这场被认为是改变中国历史的战役中,谢安挥洒自如,尽显风流。据 <<晋书-谢安传>>载,当淝水之战的捷报传来时,他正在与人下棋。看完军书后面无表情,继续落子。别人忍不住问他,他只淡淡地说:“小儿辈遂已破贼。”其镇静如此。 这位挽狂澜于既倒,救东晋社稷于将倾的人物,他的府第也在乌衣巷。 第一次,乌衣巷吸引了历史的目光。 可以想象,乌衣巷作为当时权倾朝野的大臣的宅邸,作为贵族士大夫的集居地,该是怎样一副热闹繁华的景像!高门大宅,宝马香车。白天画檐若云,晚上灯花如雨。更重要的是,这里已经不仅仅是豪族的院落,这里已经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道不可缺少的风景线。今天当我们回头去看的时候,我们都会惊叹那时候王谢两族子弟的文彩风流。在我们的记忆中,恐怕再没有哪两个家族可以涌现出那样多的人物在文化史上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恐怕再没有哪个地方会像乌衣巷那样,在短短的一段时间里集中了那么多的史笔留名的身影。人们常说千古风流,首推魏晋人物晚唐诗,东晋南北朝的乌衣巷里,哪怕我们只轻轻一瞥,也已是星光满眼。 乌衣巷
谢安,刚刚提到过的淝水之战的指挥者,少年就以风流倜倘闻名。史载他好为洛下书生咏,因为有鼻炎所以声音浓浊,竟成为时髦,导致人们都捏着鼻子学。其性格文静有儒将风度,除了东山再起的典故与其有关外,投鞭断流,风声鹤唳等由淝水之战出典的成语亦是拜他所赐。 谢道韫,安西将军谢奕之女,有名的才女。曾经用“不如柳絮因风起”来形容雪,传为名句。后来嫁给王羲之之子王凝之,对其平庸感到不满,感叹:“实不知天壤之下,竟有此王郎”。成为成语“天壤王郎”的出典。 谢灵运,谢安的孙子,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诗人,山水诗流派的鼻祖。其诗被誉为有如芙蓉出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的名句流传千年,不知倾倒过多少文人墨客。 谢惠连,谢灵运的族弟,南朝宋的诗人。当时颇有文名。 谢眺,又称小谢,南朝齐的诗人,高祖为谢安之兄。山水诗的发展者,极负诗名。据说齐帝萧衍就曾说过:“三日不读谢眺诗,便觉口臭。”唐朝诗仙李白对他极为推崇,诗文中屡屡提及,赞颂不已。后人甚至有李白“一生低首谢宣城”的说法。与谢灵运谢惠连并称“三谢”。 王族方面,书圣王羲之名满天下,他是王导从弟之子。作品<<兰亭序贴>>向来被认为是“天下第一行书”。 王献之,王羲之之子,亦是书法名家。有“小圣”之称。与其父合称二圣,都是书法史上一流的人物。 王氏中的王坦之,王徽之,王凝之也都不是无名之辈,各种故事流传至今。 乌衣巷 另外,当时在建康的名流还有著名的诗人颜延年,沈约,,编<<昭明文选>>的萧统太子,著<<文心雕龙>>的刘勰,<<诗品>>的作者钟嵘。成语“画龙点睛”的主角画家张僧繇。如果把范围再放宽,更可以举出数学家祖冲之,天文学家虞喜,化学家葛洪,医学家陶景弘,哲学家,著<<神灭论>>的范缜以及高僧法显等等。这些人在建康,或多或少地都会同高级住宅区--乌衣巷发生关系。 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如余秋雨所说,这些人在各自的领域几乎都称得上是开天辟地的巨匠。在时代的风云际会中,乌衣巷亲眼地目睹了这一切。这是乌衣巷的,它的名字随着这一大批天才的青史留名,已经同样被写进历史,再也抹不去了。 今天重修后的王谢古居,分为来燕堂,听筝堂和鉴晋楼。“来燕”取自当年谢安以燕传信的故事,听筝堂是当年晋孝武帝临幸谢宅听谢安弹古筝之地。“鉴晋”则分明有“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意思。匾额上的大字均以隶体书写,大有魏晋遗风。建筑里面有着东晋的雕刻展,东晋起居室,淝水之战的壁画,竹林七贤图和顾恺之作品<<洛神赋>>的复图,以及仿兰亭的曲水流觞渠等。也都颇可以重见到魏晋人物的风。而楼上则是个秦淮历史的展览室。 走出王谢古居,仍然回到乌衣巷的那条青石小路上来。两旁青砖小瓦,回廊挂落,一栋栋建筑起伏有序,浑然一体,应该是很优美壮观的了。可仍然让人感觉有些不适,觉得太新了,反倒希望它有些沧桑的味道才好。刘禹锡的句子不知怎地,好像总是在心中徘徊不去。 六朝的金粉和风流,给秦淮河和乌衣巷涂抹上了最绚丽的色彩。然而,随着一个时代的坍塌,乌衣巷的神话,乃至金陵六朝帝王都的神话盛极而衰。 公元581年,隋灭陈,统一全国。金陵城破之日,六朝宫阙一朝焚毁。大火连绵,数日不息。为了防止在金陵出现割据,金陵被降为到一般州县的地位。此时的王谢显族,早已颓荒败落,那似乎流光溢彩的秦淮河,也已不复往日风。隋朝国祚甚短,不久被所灭。兵火连年,战乱不断,于是六朝的古迹,繁华的往昔被摧毁得灰飞烟灭,取而代之的是断垣残瓦,满目疮痍。乌衣巷的高府华第早就踪影无存,遍地野草,焦土昏鸦,只有淮水仍在,也只是流淌着一片凄凉。 乌衣巷似乎要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或许多年以后,只有从前人那意兴湍发的诗句里,只有从六朝那流金错彩的骈句中,我们才能重新找到有关它的只言片语。想像它的如梦繁华,然后发出一声巴比伦式的叹息吧。 可是就这一片废墟,竟然还是有人来。 而且来的还不是一般的人。 李白,崔颢,刘禹锡,杜牧,李商隐,韦庄。唐朝最伟大的几位诗人,到金陵一游。 南唐之后,宋元两朝,仍然不断地有人来。 王安石,周邦彦,朱敦儒,萨都剌,等等。宋元最有名的几位词人,来金陵登访。 他们都是来怀古的。 忽然间,金陵怀古就不单单是一个简单的诗词题材了。忽然间,它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专门的课题,成了一种特有的,一个洋洋大观的体系。这在文学史上,绝对是独一无二的。忽然间,中国的文化出现了一个奇观。 李白来到金陵,他登上凤凰台,眺望白鹭州,然后说:“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登金陵凤凰台>>) 千古名句,千古名作。 杜牧来了,他夜晚停泊在秦淮河上,听见弦歌声声,于是说:“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泊秦淮>>) 又是句千古名句,又是首千古名作。 而乌衣巷,则终于等来了刘禹锡,等来了“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等来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乌衣巷
铅华洗去,落尽了飞红。六朝的脂粉随着秦淮河的河水东去再不复返。繁华的旧梦随着笙歌的散尽再不重来。现在的乌衣巷已然物事两非了,那原本富丽堂皇的朱雀桥边,早就杂草丛生,颓败不堪;那原本庄严气派的乌衣巷口,只剩下如血的残阳夕照。当年的王谢世族几多风流人物,如今却安在呢?现在这里只有一片废墟,摇摇欲坠的矮房里住着最最寻常的百姓。只有那飞来飞去的燕子,好像还似曾相识,是为了见证这沧海桑田而留下的吧。 全诗看似藏而不露,可是历史的苍凉,人世的无常,富贵荣华的白云苍狗,功名荣辱的身后寂寞在这首七言绝句里被剖白前所未有地透彻,前所未有地沉痛,无奈,充满了宿命感。 文学史在这一刻记住了乌衣巷。从这一刻起,后世所有的文人,学者,官吏,学生,百姓,只要他或她面对文学,就无法逃开乌衣巷的名字。 刘禹锡在离开前最后望了那残破的巷陌一眼。他却不知道,那一刻,乌衣巷在野草和废墟中重生了。那一刻,乌衣巷不再需要任何砖瓦去重建,它已经得到了永恒。 除了<<乌衣巷>>,刘禹锡在金陵还留下了其他名句。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石头城》)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西塞山怀古》) …… 李后主的悲剧过后,宋朝元朝的词人又来了。 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怀古>>在三十多首同名词中脱颖而出: …… 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 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 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 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宫遗曲。 据说苏东坡读到这首词后感叹:此老乃野狐精也。 宋词的集大成者周邦彦则表现出难得一见的悲壮: …… 空余旧迹,郁苍苍,雾沈半垒。 夜深月过女墙来,伤心东望淮水。 酒旗戏鼓甚处市?想依稀王谢邻里。 燕子不知何世,向寻常巷陌人家相对,如说兴亡斜阳里。 (《西河-金陵怀古》) 元朝的词人萨都剌更是把怀古一题发挥到淋漓尽致: 六代豪华,春去也,更无消息。 空怅望,山川形胜,已非畴昔。 王谢堂前双燕子,乌衣巷口曾相识。 听夜深,寂寞打孤城,春潮急。 …… 乌衣巷
(《满江红-金陵怀古》) 乌衣巷和王谢堂在这些千古名作间被升华了,乌衣巷已经不再是一条小巷了,它业已成为金陵兴亡的象征,业已成为古今变迁的代言。乌衣巷在不知不觉之间,有了一种沧桑的,带着历史深沉的气味。乌衣巷,已经深深地刻入了中华文化的肌肤之中,融入到它的血液里面,再也分不开了。 于是,乌衣巷是否依旧繁华或者还是一堆废墟,已经变得不再重要,甚至是否还有这么一条巷,都已经没人关心。只要有它的名字在,就会有人千里来吊,就会有人感慨着赋出一首又一首的新诗或新词,甚至会有人无端端地因它而落下两行清泪来,作为对文化深深的祭奠。 如果说王导和谢安令乌衣巷不凡;王羲之,王献之,谢灵运令乌衣巷不俗,那么刘禹锡,周邦彦和萨都剌则令它不朽。 一堆废墟的般的不朽。 然而至此乌衣巷的故事仍没有结束,因为南京实在是个多灾多难的城市。 朱元璋来了,作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从南方起家的皇帝,他把都城定在了南京。被今人视为珍宝的南京城墙修建起来了。然而朱元璋死后没过多久,明成祖朱棣起事,把建文帝赶下了台,然后拖着大批的珍宝美女到北京筑他的紫禁城去了。 于是南京似乎无事了,秦淮河两岸一天比一天热闹起来。达官显臣,豪商巨富,纷至沓来;琼楼玉阁,舞榭歌台,鳞次枳比。白天烟花流水,晚上月照婵娟,虽然已没有了乌衣巷,秦淮也似乎又回到六朝时的鼎盛了。野草和夕阳已经从人们的眼里淡去,取而代之的是椒蓝红粉,画舫妓楼,纸醉金迷。虽然秦淮河边还有一个叫吴敬梓的人在奋笔疾书,想用一部<<儒林外史>>来表达些什么,可是根本没人听他的,也没有人理睬他。“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在明眸流盼里,在觥筹交错中,刘禹锡用笔深刻在文化骨子里的乌衣巷,好像要一点点地被这桃花美酒腐蚀掉了。直到有一天,大明江山突然开始土崩瓦解。 这一段历史是一段的历史。这中间经过了多少斗争,抵抗,挣扎,呐喊,多少人为了民族的气节舍生取义,已经是不可能数清的了。今天的历史学家都不约而同地指出,在明亡前的这一段时间里,已经腐败到了极点,精神上堕落到极点的明王朝,却反而在临终前呈现出一种反常的悲壮和慷慨。今天我们读史,对当时发生在十里秦淮边的故事几乎有眼花缭乱的感觉。突然之间,所有的道德理念全都翻了个个;突然之间,烟花女子成了历史的主角。明亡的历史如果仅仅是刑场上的袁崇焕,仅仅是煤山上的崇祯,仅仅是史可法的扬州城,那么,我们可以说它悲壮。可是如果还有奋身想往水池里跳的柳如是和嫌水太冷不能下的大学士钱谦益,如果还有为忠义奔走的说书人柳敬亭和终于投降的公子候方域,如果还有李香君般的溅血桃花和最后无奈的“桃花扇底送南朝”的喟叹,我们可以说出的就不止是悲壮 ,更有悲哀了。明亡的历史是前所未有的沉痛的历史。 于是金陵古都除了沧桑兴替的慨叹,更开始多了悲凉苦痛的色彩。 又过了200多年,1842年,清在南京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不久太平天国兴起,定南京为天京。相持11年后,清军于1867年破城,大,并放火焚烧。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定南京为临时国都。经过十余年军阀混战后,1927年复都南京,此时秦淮两岸早已是藏污纳垢,混乱不堪。 再过10年,1937年日军攻占南京,展开灭绝人寰的大。死难者达30万人。秦淮古溪为尸体填塞。六朝胜地付之一炬,金陵王气黯然尽收。南京几乎到达了历史上的最低点。 冥冥间似乎又是一个轮回。从盛极一时到繁华落尽。 只是这次不再仅仅是历史的兴替,这次更是民族和国家的命运;这次人们凭吊的不再只是荣辱兴废的感慨,更是生死存亡的感悟。这次,不再是乌衣巷的盛衰或金陵城的盛衰,这次,是中华民族的盛衰。 站在乌衣巷口凭吊这段痛史,心里明明知道乌衣巷自唐以来便已多半废弃,明清民国的战事血火,似乎与它扯不到一起。可又始终无端地觉得它也应是这些悲惨历史的见证人,觉得如果要在乌衣巷口怀古凭吊的话,这段历史是理所当然包括在内的。于是猛然发觉在脑海中,乌衣巷和金陵已经紧紧连在一起,再也分不开了。突然又觉得那些千古的吊亡感怀诗,不管是在哪里作的,何时作的,也都与乌衣巷紧紧连在一起,再也分不开了。 我深呼一口气,抬眼望去。只见天色渐晚,暮霭沉沉。 历史终于翻开了新的一页。 1949年4月,解放军占领南京。 年起,开始冲洗秦淮河的污水,使之碧波重现。并开始建设秦淮河旅游风光带。 4年前,也就是19年,乌衣巷荒废千年以后,终于还是和王谢堂一起重建了,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模样。 而更早些时候,诗人笔下的那早已湮没的朱雀桥也已再次跨立在秦淮河上。位于原来的镇淮桥和武定桥之间,仿佛存心要勾起游人的情绪般的。 十里秦淮又开始喧攘如初。 夕阳西下,乌衣巷变得沉重起来。巷子的另一头通往的是白鹭州公园,然而如今因为秦淮变窄,再也看不到李白笔下“二水中分白鹭州”的景色了。于是从原先的路返回,迎面看到的秦淮河依旧美丽,河中依然有画舫灯船,河对岸的明九龙壁流光溢彩,栩栩如生。两岸上,媚香楼,得月台,晚晴楼的招牌是那么地诱人。夫子庙前也依旧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突然觉得,秦淮河应该一直是那样美丽的,不管人事是兴是衰,她总是可以那样地风情万种。难怪明末爱国诗人顾梦游即使在明亡后回游秦淮,依然有“杨柳风千树,笙歌月一船”这样清丽的句子;难怪朱自清和俞平伯在那样的年代,怀着那么浓的愁绪去写秦淮河,笔下仍然流出醉人的风韵来。就好像中山陵总应该是雄壮的,莫愁湖总应该是艳婉的,夫子庙总应该是热闹的一样。 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金陵的历史,金陵的感叹,金陵的伤痕,金陵的沧桑又该向何处去寻呢? 回头再看了一眼乌衣巷。那块诗碑依然屹立。上面的字笔走龙蛇,遒劲不凡,是的亲笔书法,录的自然还是刘禹锡的那首名作了。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突然又相信,乌衣巷如同秦淮河一样,也是一直没有变过的。自从诗人落下了他手中的笔,乌衣巷就注定了要承担这个城市乃至这个文化的感叹。无论它是兴,是衰,是新,是旧,还是一堆废墟,乌衣巷的形象并不因此而改变的。有和无都是虚幻,乌衣巷已经是永恒。 于是不禁笑自己刚才的拘泥。转身离去,眼前仿佛又出现1300年前,诗人奋笔疾书的身影。那一刻,乌衣巷获得了永生。
一、开封
它背靠一条黄河,脚踏一个宋代,像一位已不显赫的贵族,眉眼间仍然器宇非凡。
省会在郑州,它不是。这是它的。曾经沧海难为水,老态龙钟的旧国都,把忙忙颠颠的现代差事,洒脱地交付给邻居。
陪同我的人说,宋史上记载的旧地名,都在今天开封地底下好几公尺。黄河经常决水,层层淤泥堆积,把宋代繁密的脚印深深潜藏。庞贝古城潜藏得过于轰轰烈烈,中国人温文尔雅,连自然力也入乡随俗,一层层地慢慢来。开封古都,用灾难的刷把,一次次刷新。人们逃了又来了,重新垦殖,重新营建,重新唤醒古都气韵,重新召来街市繁荣。开封最骄傲的繁荣,见之于《清明上河图》。
开封就像我们整个民族,一再地在灾难的大漠上重新站立,立誓恢复淤泥下的昔日繁华。但是,淤泥下的一切属于记忆,记忆像银灰色的梦,不会有其它色彩。于是,开封成了一个褪色的遗址。
只有最高大、最坚牢的构建未曾掩埋。台阶湮没了,殿身犹在;高塔被淤没底层,仍然巍然不摧。那天我与友人同去开封,不知爬了多少台阶,古塔、古塔、古塔,宫殿、宫殿、宫殿。我累了,上下环顾,对友人说:“我真想把荒草间的石阶拍下来,题名时间。”友人说:“别拍了,一端相机便成了现代。”
倒也是。时间的力量只能靠着体力慢慢去爬、去体会,不能拿着一张照片轻松地去看。一轻松,全都变味。
国内许多古塔已经禁止人们攀援,而开封古塔却听便。不必过于担心有无数的人在塔中拥挤,爬塔是一种体力和意志的考验。塔阶很窄、很陡、也很暗,不拼力爬到每层的窗洞口你不可能停下,到了窗洞口又立即产生更上一层观看的渴念。爬塔心理可以构成一种强烈的悬念线,塔顶塔尖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召唤。要么不进塔。进了它,爬了它,很少有人半途而返。让体力心力不济的人们静静仰望吧,塔身中天天地进行着青春和生命的接力赛。千年前建塔的祖先们,不经意地留下了物理上和心理上的两个制高点,来俯矙一代代的子孙是否有点出息、有点能耐。当我爬到最后一层,我真想气喘吁吁地叫一声:“我报到,我的祖先!”
是的,只有远远高于现实的构建,总有能力召唤后代。
二、南京
六朝金粉足能使它名垂千古,何况它还有明、清两代的政治大潮,还有近代和现代的殷殷血火。
许多事,本来属于全国,但一到南京,便变得特别奇崛,让人久久不能释怀。历代多得很,哪像明末清初的“秦淮八艳”,那样具有文化素养和政治见识,使整整一段政治文化史都染上了艳丽色彩?历代农民起义多得很,哪像葬身紫金山的朱元璋和把南京定都为天京的洪秀全,那样叱咤风云,闹成如此气象?历代古都多得很,哪像南京,直到现代还一会儿被外寇血洗全城,一会儿在炮火中作历史性永诀,一次次搞得地覆天翻?
中华民族就其主干而言,挺身站起于黄河流域。北方是封建王朝的根基所在,一到南京,受到楚风夷习的侵染,情景自然就变得怪异起来。南京当然也要领受黄河文明,但它又偏偏紧贴长江,这条大河与黄河有不同的性格。南京的怪异,应归因于两条大河的强力冲撞,应归因于一个庞大民族的异质聚汇。
这种冲撞和聚汇,激浪喧天,声势夺人。因此,南京城的气魄,无与伦比,深深铭刻着南北交战的宏大的悲剧性体验。玄武湖边上的古城墙藤葛拂拂,明故宫的遗址仍可寻访,鸡鸣寺的锺声依稀能闻,明孝陵的石人石马巍然端立,秦淮河的流水未曾枯竭,夫子庙的店铺重又繁密,栖霞山的秋叶年年飘落,紫金山的架势千载不移,去中山陵、灵谷寺的林荫道,永远是那样令人心醉。
别的故都,把历史浓缩到宫殿;而南京,把历史溶解于自然。在南京,不存在纯粹学术性的参观,也不存在可以舍弃历史的游玩。北京是过于铺张的聚集,杭州是过于拥挤的沉淀,南京既不铺张也不拥挤,大大方方地畅开一派山水,让人去读解中国历史的大课题。我多次对南京的朋友说,一个对山水和历史同样寄情的中国文人,恰当的归宿地之一是南京。除了夏天太热,语言不太好听之外,我从不掩饰对南京的喜爱。
心中珍藏的千古名诗中,有不少与南京有关,其中尤以刘禹锡的《石头城》为最: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
1000多年前的诗人已把怀古的幽思开拓到如此气派,再加上1000年,南京城实在是气可吞天。
三、成都
对整个中国版图来说,群山密布的西南躲藏着一个成都,真是一种大安慰。
我初次入川,是沿宝成铁路进去的。已经看了那么久的黄土高原,连眼神都已萎黄。山间偶尔看见一条便道,一间石屋,便会使精神陡然一震,但它们很快就消失了,永远是寸草不生的连峰,随着轰隆隆的车轮声缓缓后退,没完没了。也有险峻的山势,但落在一片灰黄的单色调中,怎么也显现不出来。造物主一定是打了一次长长的瞌睡,把调色板上的全部灰黄都倾倒在这里了。
开始有了隧洞,一个接一个,过洞时车轮的响声震耳欲聋,也不去管它,反正已张望了多少次,总也没有绿色的希望。但是,隧洞为什么这样多呢,刚刚冲出一个又立即窜进一个,数也数不清。终于感到,有这么隆重的前奏,总会有什么大事情要发生了。果然,不知是窜出了哪一个隧洞,全车厢一片欢呼:窗外,一派美景从天而降。满山绿草,清瀑飞溅,黄花灼眼,连山石都湿渌渌地布满青苔。车窗外成排的桔子树,碧绿衬着金黄,硕大的桔子,好像伸手便可摘得。土地黑油油的,房舍密集,人畜皆旺。造物主醒了,揉眼抱愧自己的失责,似要狠命地在这儿补上。
从此,我们一刻也不愿离开车窗,直至成都的来到。
有了一个成都作目的地,古代的旅行者可以安心地饱尝入川的千里之苦了。蜀道虽难,有成都在,再难也是风雅,连瘦弱文人也经受得了。
中华文明所有的一切,成都都不缺少。它远离东南,远离大海,很少耗散什么,只知紧紧汇聚,过着浓浓的日子,富足而安逸。那么多山岭卫护着它,它虽然也发生过各种冲撞,却没有卷入过铺盖岛的大灾荒,没有充当过赤地千里的大战场。只因它十分安全,就保留着世代不衰的幽默;只因它较少刺激,就永远有着麻辣的癖好;只因它有飞越崇山的渴望,就养育了一大批纔思横溢的文学家。
成都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丰盈偏仓。这里的话题甚多,因此有那么多茶馆,健谈的成都人为自己准备了品类繁多的小食,把它们与历史一起细细咀嚼品尝。
成都的名胜古迹,有很大一部分是外来游子的遗迹。成都人挺大方,把它们仔细保存,恭敬瞻仰。比之于重庆,成都的沈淀力强得多。正是这种沈淀力,又构建了它的稳健。重庆略嫌浮嚣。
重庆也有明显的长处,它的朝天门码头,虎虎地朝向长江,遥指大海,通体活气便在这种指向中回荡。沈静的成都是缺少这种指向的,古代的成都人在望江楼边洒泪揖别,解缆挥桨,不知要经过多少曲折,纔能抵达无边的宽广。
成都的千古难题至今犹在:如何从深厚走向宽广?
四、兰州
常听人说,到西北最难适应的是食物。但我对兰州印象最深的却是两宗美食:牛肉面与白兰瓜。
因此,这座黄河上游边的狭长古城,留给我两种风韵:浓厚与清甜。
兰州牛肉面取料十分讲究,一定要是上好黄牛腿肉,精工烹煮,然后切成细丁,拌上香葱、干椒和花椒;面条粗细随客,地道的做法要一碗碗分开煮,然后浇上适量牛肉汤汁,盖上刚刚炒好的主料。满满一大碗,端上来面条清齐、油光闪闪、浓香扑鼻。一上口味重不腻,爽滑麻烫。另递鲜汤一小碗,如若还需牛肉,则另盘切送,片片干挺而柔酥,佐蒜泥辣酱。在兰州吃牛肉面,一般人都会超过平时的食量。
我兰州的朋友范克峻先生是一位历尽磨难之人,经常带我到一家铺子吃牛肉面。掌勺的马师傅年事已高,见范先生来便亲自料理一切,不容有半点差池。范先生轻声告诉我,这位马师傅实在是一位侠义之士,别看他每天只是切肉煮面,你完全可以把一切信托于他。30多年前,一位每天到这儿吃面的演员突然遭冤被捕,关在监狱里,判刑不轻。妻子亲朋都离他而去,过年过节时也没人来探望。他万万没有想到,竟然是这位马师傅出现在铁窗之前,手提一包干切牛肉,无言捧上。如此者每年不断,一直延续整整20年之久。20年后,演员的冤案昭雪平反,他又重登舞台,名震全城。不管他用什么方式来邀请和感谢,马师傅全不接受,只在他每天早晨来吃牛肉面时,投以轻轻一笑。
正说着,马师傅的牛肉面已经煮好端来,只一口,我就品出兰州的厚味来了。
在风味上,白兰瓜与牛肉面正恰构成强烈对比。这种瓜吃时须剖成长条,入口即满嘴清凉,味不浓,纔嚼几下就消融在咽喉之间,立时觉得通体润爽。据说白兰瓜是外来品种,兰州接纳了它,很快让它名扬中华。兰州虽然地处僻远的西北,却是闻名的瓜果之乡。只要是好瓜好果大多都能在兰州存活,而且加添上一份香甜。火车经过兰州站,车厢里会变戏法一样立即贮满了各种瓜果,性急的旅客立即取刀削食,满车都是甜津津的清香。
瓜果的清香也在兰州民风中回荡。与想象中的西北神貌略有差异,这儿的风气颇为疏朗和开放。衣着入时,店货新潮,街道大方,书画劲丽,歌舞鼎盛,观众看戏的兴趣也洒脱的正常。京剧、越剧、秦腔都看,即便是演一个外国话剧,票房价值仍然很高。去敦煌必须经兰州,因此在兰州的外国旅游者很多。兰州的一大缺憾,是机场离市区实在太远,极为不便;但兰州机场女播音员的英语水平,在我听来,在全国机场之上,这又给国际友人带来了一种舒坦。
这便是兰州,对立的风味和谐着,给西北高原带来平抚,给长途旅人带来慰藉。中华民族能在那么遥远的地方挖出一口生命之泉喷涌的深井,可见体力毕竟还算旺盛的。有一个兰州在那里驻节,我们在穿越千年无奈的高原时也会浮起一丝自豪。
五、广州
终究还得说说广州。
前年除夕,我因购不到机票,被滞留在广州、许多朋友可怜我,纷纷来邀请到他们家过年。我也就趁机,轮着到各家走了走。
走进每家的客厅,全是大株鲜花。各种色彩都有,名目繁多,记不胜记。我最喜欢的是一株株栽在大盆里的金桔树,深绿的叶,金黄的果,全都亮闪闪的。一位女作家顺手摘下两枚,一枚递给我,一枚丢进嘴里。她丈夫笑着说:“不到新年,准被她吃光!”而新年就在明天。
那天下午,几位朋友又来约我,说晚上去看花市,除夕花市特别热闹;下午就到郊区去看花圃。到花圃去的路上,一辆一辆全是装花的车。广州人不喜爱断枝摘下的花,习惯于连根盆栽,一盆盆地运。许多花枝高大而茂密,把卡车驾驶室的顶都遮盖了,远远看去,只见一群群繁花在天际飞奔,神奇极了。这些繁花将奔入各家各户,人们在花丛中斟酒祝福。我觉得,比之于全国其它地方,广州人更有权利说一句:春节来了!
可惜,从花圃回来,我就拿到了机票,立即赶向机场,晚上的除夕花市终于没有看成。
在飞机上,满脑子还盘旋着广州的花。我想,内地的人们过春节,大多用红纸与鞭炮来装点,那里的春意和吉祥气,是人工铺设起来的。唯有广州,硬是让运花车运来一个季节,把实实在在的春天生命引进家门,因此庆祝得最为诚实、最为透彻。
据说,即便在最动荡的年月,广州的花市也未曾停歇。就像广州人喝早茶,天天去,悠悠然地,不管它潮涨潮退、云起云落。
以某种板正的观念看来,花市和早茶,只是生活的小点缀,社会大事多得很,哪能如此迷醉。种种凌厉的号令远行千里抵达广州,已是声威疏淡,再让它旋入花丛和茶香,更是难以寻见。“广州怎么回事?”有人在吆喝。广州人好像没有听见,嘟哝了一声很难听懂的广州话,转身唤了嗅花瓣,又端起了茶盏。
广州历来远离京城,面对大海。这一方位使它天然地与中国千年封建传统构成了逆反。千里驿马跑到这里已疲倦不堪,而远航南洋的海船正时时准备拔错出发。
当驿马实在搅得人烦不胜烦的时候,这儿兀兀然地站出了康有为、、黄遵宪、孙中山,面对北方朗声发言。一时火起,还会打点行装,慷慨北上,把事情闹个青红皂白。北伐,北伐,广州始终是北伐的起点。
北上常常失败。那就回来,依然喝早茶、逛花市,优闲得像没事人一样,过着世俗气息颇重的情感生活。
这些年,广州好像又在向着北方发言了,以它的繁忙,以它的开放,以它的勇敢。不过这次发言与以前不同,它不必暂时舍弃早茶和花市了,浓浓冽冽地,让慷慨言词拌和着茶香和花香,直飘远方。
像我这样一个文人,走在广州街上有时也会感到寂寞。倒也不是没有朋友,在广州,我的学生和朋友多得很,但他们也有寂寞。我们都在寻找和期待着一种东西,对它的创造,步履不能像街市间的人群那样匆忙,它的功效,也不像早茶和花市,只满足日常性、季节性的消耗。